
自2025年10月14日起,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正式对中国籍或中国建造的船舶征收“港口入港费”。该政策以船舶属性为核心划分标准,旨在通过分层费率调整航运结构与供应链依赖。具体征收分为三档:
其一,对中资运营/船东的船舶,按净吨(NT)每航次收费50美元/NT,并自实施日起每年递增30美元,至2028年将升至140美元/NT。此费用按“每艘船、每次进入美国港口”征收,每年每船最多计费5次。其二,对中国建造的非中资运营船舶,采用“孰高原则”征收:按净吨18美元/NT或按每个卸下集装箱(TEU)120美元,两者取其高者。该费率同样逐年提高,至2028年净吨费达33美元/NT,按箱计费升至每箱250美元。其三,对外国建造的车辆运输船(汽车/滚装船),无论是否与中国有关,统一按净吨14美元/NT征收。
政策同时设有豁免条款,美国籍船舶、参与美国海事管理局(MARAD)特定项目的船舶、小型船舶(载箱量低于4000 TEU或载重低于5.5万吨)以及空载或压载驶入的船舶均可获得豁免。此外,由于美国目前缺乏本土液化天然气(LNG)船建造能力,因此LNG运输船享有过渡期,暂不征费,但美国计划自2028年起强制要求其出口的LNG必须由一定比例的美国建造船舶承运,并在未来22年内逐步提升比例(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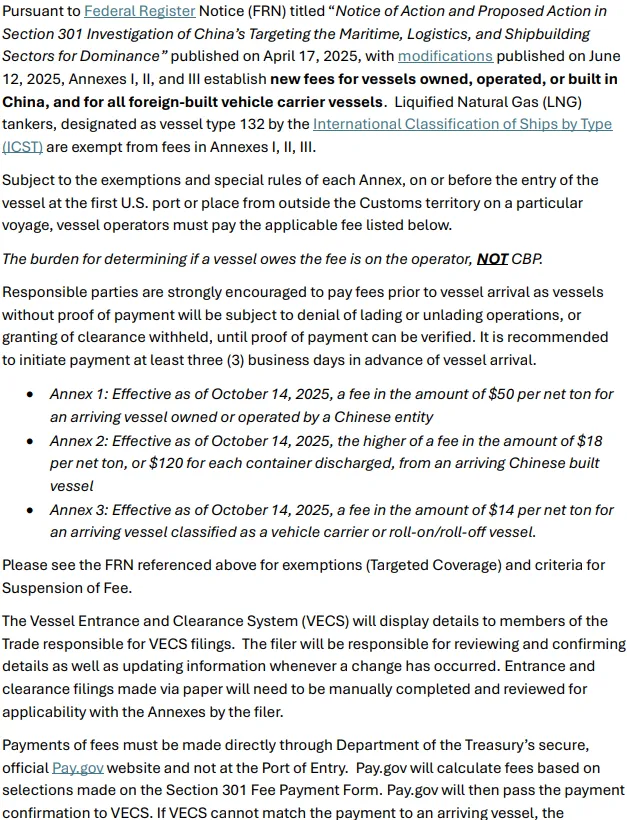
图源:Federal Register Notice
该政策的落地并非仓促出台,而是历经一年半的调查、听证与立法程序逐步推进。2024年4月17日,USTR启动对中国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启动“301调查”。随后在2024年5月29日,USTR举行了首次公开听证并征求意见。2025年1月16日,USTR发布调查报告,认定中方相关做法“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为后续措施提供了依据。
2025年2月27日,USTR在《联邦纪事》上公布了拟议措施并开启公众评议;同年3月24日至26日,又举行了第二轮听证。4月9日,美国总统签署第14269号行政命令:“恢复美国海运主导地位”,为征费与配套执法定框架。4月17日,USTR在《联邦纪事》发布正式通知,确定对“中国相关船舶”征收港口费,并设置180天过渡期。
随后9月29日,中方修订《国际海运条例》,授权对歧视性措施反制。10月3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发布操作指引,明确要求通过Pay.gov预缴费用,并建议船舶在靠港前至少3个工作日完成,否则可禁装卸/延迟放行。10月7日,即新规生效前一周,美国官方与行业媒体确认将按期执行,并提醒相关方自查与预缴。最终在10月14日正式生效,截至目前,政策未见延迟迹象,新政进入正式执行阶段。
▌为何瞄准中国航运与造船业?
这项政策出台,体现了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与产业竞争。自2018年以来,美国多次运用301条款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如今美国政府进一步将贸易战“武器”延伸到服务领域,对准海运业这一中国优势产业。这一举措与特朗普政府整体对华强硬基调一致,旨在遏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战略行业的主导地位。美国贸易代表在公告中直言,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在公海上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
同时,美国官员认为,过度依赖中国造船厂和航运,会带来供应链脆弱性和安全隐患。一方面,中国造船业规模庞大且与军事工业联系紧密,美国每年新造商船不到10艘,而中国船厂年建造商船超过1000艘。中国还掌控大量远洋商船,运营全球重要航线。在危机或冲突情况下,美国担心对中国制造的船舶、设备(如港口大型起重机)以及中国航运服务的依赖,可能演变为战略劣势。因此,特朗普政府认为有必要从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链自主出发,限制中国在美国海运领域的影响力。
此外,政策另一大考量是借机提振美国本土造船能力,恢复就业和产业竞争力。港口费产生的收入将上缴美国财政,据称将用于支持重振美国产业。国会正推动相关立法建立专项基金,且获得两党支持。行政命令和301行动方案中也包含激励措施:如果运营商订购美国建造的新船,可暂缓缴纳最多三年的费用。这类“以费促产”的机制,旨在向市场发出需求信号,鼓励航运公司采购美国或盟国建造的船舶。长远看,美国希望借此逐步扭转商船建造几乎完全依赖东亚(特别是中国)船厂的局面。
▌成本冲击波下,中美贸易转移与航线洗牌
根据航运情报机构Alphaliner的分析,新规预计将为全球集装箱航运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新增成本。仅前十大全球班轮公司在2026年的合计支出就可能高达约32亿美元。若费用无法顺利转嫁,中资航运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受到显著挤压。据测算,每个20英尺标准箱(TEU)平均将增加约120至150美元的额外成本,大型进口商可通过规模效应分摊压力,但对利润有限的中小出口商而言,这将成为切实的经营负担。
在运营层面,新规正迫使全球航运企业重新布局中美航线网络。班轮公司开始在联盟框架下优化船舶配置,尽量以非中资、非中造船舶执行美国航线。同时,为规避费用,第三国中转方案增多。北美邻国港口有望成为新的中转节点,货物可先在加拿大或墨西哥卸船,再经陆路进入美国,从而绕开美方直接收费。随着中转量上升,这些区域性枢纽港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北美航线结构或将从以直挂美西、美东为主,转向“邻接国中转+跨境运输”的新模式。
从贸易上看,港口费提高无疑增加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成本,进而影响双边进出口的节奏与规模。短期内,美国进口商可能提前囤货以避开新规初期的混乱,或观望政策谈判进展,导致进口节奏出现异常波动。中期来看,若费用长期存在且逐年递增,中国出口商的竞争优势将被削弱。部分低货值、高体积商品(如家具、建材等)因海运成本上升而面临被迫退出美国市场的风险,企业可能转而布局东南亚、拉美等替代市场,以分散对美依赖。与此同时,美国进口商也将加速供应链多元化,从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增加采购,以降低对中资航运的依赖与风险暴露。
在班轮运输市场上,新规或将重塑全球运营商格局。中国国有航运公司因承担高额费用,其美线利润空间将被大幅压缩。若缺乏政策支持或补贴,削减航班与提价转嫁几乎不可避免。相对而言,非中资航运公司由于船队中中造船占比较低,受影响较小,可能借机以更低成本运营美线服务,从而承接部分转移出的货载,扩大市场份额。长远来看,全球航运业或将出现明显的“两极化”:一极是尽量剥离中国要素、专注美欧日市场的“西方阵营”航运公司;另一极则是深耕“一带一路”及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中资航运企业。此种分化将重塑远东-北美航线的竞争与合作格局。
美国市场运输壁垒的上升,也将推动区域贸易与替代市场的崛起。中国对东盟、非洲、拉美的出口可能相对增加,以弥补对美市场的增速放缓;而美国则会加快推进“近岸采购”与“友岸外包”战略,把部分供应链环节迁至墨西哥、加拿大等友好国家,从源头上减少跨太平洋航运需求。而北美内部贸易及北美-拉美航线量将上升,跨洋长程运输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如果中国采取对等港口费措施,美国出口商(如农产品、能源)将面临额外成本压力,部分货物可能转往其他买家或经第三地转运。这些变化叠加,中美双边贸易增速可能放缓,贸易流向趋向多元化。
▌跨境卖家:时效、成本与供应链稳定性承压
美国新政对依赖海运的跨境卖家在短中期内将产生多方面影响:
物流时效:由于政策突然性和不确定性,航运公司需要调整船期和航线以应对新规,可能导致运输时效波动。首先,运营方必须在船舶抵美3天前完成费用支付,否则船舶将被禁止装卸。这增加了流程复杂性,万一支付延误或系统故障,船舶停滞港口将直接拖延货物提离时间。此外,一些航运公司为避费可能改道第三国中转,这种绕行模式将使整体运输时间拉长数天以上。对于时效要求高的卖家(例如电商旺季备货),需提早规划,以防物流链因政策生效初期的混乱而延迟。
运输成本:港口费将抬高跨境海运的总成本。根据规定,每只40英尺集装箱(按两个20英尺计)可能面临最高$240的附加费(按每20英尺标准箱$120计算)。即便以单个20尺箱$120计,也占到当前跨太平洋运费相当比例(假设运价为每40英尺箱$1500,则额外成本约8%)。对于由中资班轮公司承运的货物,费用更高:以一艘5万净吨的中国运营集装箱船为例,首航费用约$250万,相当于每个标准箱$400-$500的额外成本。虽然最终承担方如何分摊尚未明确,但航运公司很可能通过征收附加费的方式向货主转嫁部分成本。因此,跨境电商和出口商的海运费用支出将上升,利润空间被压缩。此外,保险和风控成本也随之增加:政策带来的地缘风险溢价可能反映在新的燃油附加、保险费率上,增加全程物流费用。
舱位与运力:短期内市场运力可能出现紧张或错配。一些船公司已将旗下中国建造的船调离美线,以避免费用。在政策生效初期,由于合规操作不熟练,加之部分船舶绕行,加拿大、墨西哥港口接驳能力有限,可能出现有效运力阶段性供给不足的情况。运力紧张将导致舱位竞争加剧,特别是美西传统航线。跨境卖家可能发现订舱变得困难,一箱难求的情况或再度出现。即使运力逐步恢复,调整期间的不稳定性仍可能导致卖家的出货计划面临中断风险。
服务可靠性与中断风险:港口费的实施为海运增加了一层新的地缘政治风险。S&P(标普全球)的行业报告指出,这一不确定政策让航运公司在调整船队部署时如履薄冰。卖家需注意潜在的服务中断——如中资航运公司缩减美国航线,或因中美博弈升级导致航班取消。中国政府已授权反制,如针对美籍或他国船舶征费或限航,一旦执行将进一步加剧跨境运输的不确定性。
▌航运业的“合规”求生:换船、改道与抱团
面对高昂的港口费,航运业各方该如何应对?
更换船舶/船队重组:“换船”是多数班轮公司的首选策略,将受影响的船舶从美国航线撤出,换用不在收费范围内的船舶执行美线服务。同样,中远海运可能与联盟伙伴协商,用伙伴的非中造船承运美线货物,而把自己的中造船投入其他航线。对于租赁运营的船舶,部分承租人考虑通过调整租约结构规避认定。有报道称,中国的融资租赁公司正与监管部门探讨将船舶租赁结构转换为抵押贷款,使船舶名义业主不显性为中资,从而避免被视作“中资拥有”船舶。
改变挂靠港和运输路径:调整航线挂靠以避开直接进入美国关境。可用邻国港口替代,由中资或中造船舶将货物运至加拿大或墨西哥的港口,再通过陆运或驳船将货物送入美国。这样船舶本身不进美国港口,不触发收费。当然,中转增加物流成本和时间,但如果港口费持续上涨,绕行成本相对就显得值得承担。类似地,一些承运人可能选择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中转枢纽(如巴拿马、牙买加),把远东货载在此换装到非中资船舶,再运往美国。本质上,通过“拆单分运”(把直达航程拆分成两段)来巧妙避费。从跨境卖家角度,也可通过选择转运服务,避开在美国入境的航段使用受限船舶,以降低费用摊派。
控制单船挂靠频次:由于政策规定每艘船每年最多收费5次,航运公司可优化航线班期,避免单船过于频繁地进出美国。一些较短航线(如美西-中美洲)或双港挂靠航线可能让单船年进港次数超出5次。对此,航运公司可增加船舶投入或调整挂靠频率,确保每艘船不超过收费上限,从而削减整体费用支出。此外,运营方也会尽量合并在美挂靠,使每个航次只在首个美港缴费一次(按规定,一次航线上多个美港停靠只收一笔费)。这类策略将使航次设计更偏向直挂单一美港,然后通过内陆运输分拨货物,以减少收费触发次数。
延寿非中造老船:航运公司可能推迟淘汰船队中非中国制造的旧船,即“延缓拆船”。这些老旧船舶虽然燃效较差,但胜在不受新政收费,因而成为宝贵资产。而手上有大量中国制造新船的公司会考虑船舶调拨,将这些船部署到欧洲、中东等非美国航线赚取收益,同时把不受费的船集中到美线。
加强联盟与合作:新政下,航运公司的抱团取暖更显重要。联盟内部船舶互换、舱位互供将更加频繁,中资公司依托伙伴船队维持美线服务。此外,一些运营商可能寻求代码共享或共舱协议,即让受限船舶尽量不上美线,而通过交换舱位方式继续提供服务。这种合作可确保客户服务不中断,同时分散费用成本。航运业还可能与货主紧密协商,如大型托运人签订长期合同共同分担费用,或调整供应链策略(如改用海外仓储,错峰发货)以应对运力变化。
上述种种规避策略,无论是航线重构、船队重组还是联盟协同,其本质都揭示了航运业在地缘政治博弈压力下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然而,这些战术调整的深远影响远超运营层面本身。美国对“中国相关船舶”征收高额港口费,堪称百年航运史上的重大变局。短期的震荡已现,长期的影响才刚开始显现。它既是中美战略竞争的缩影,也可能成为重塑全球物流格局的催化剂。因此,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需为一场持久的适应战做好准备,在不确定性中寻求新的平衡与机遇。

